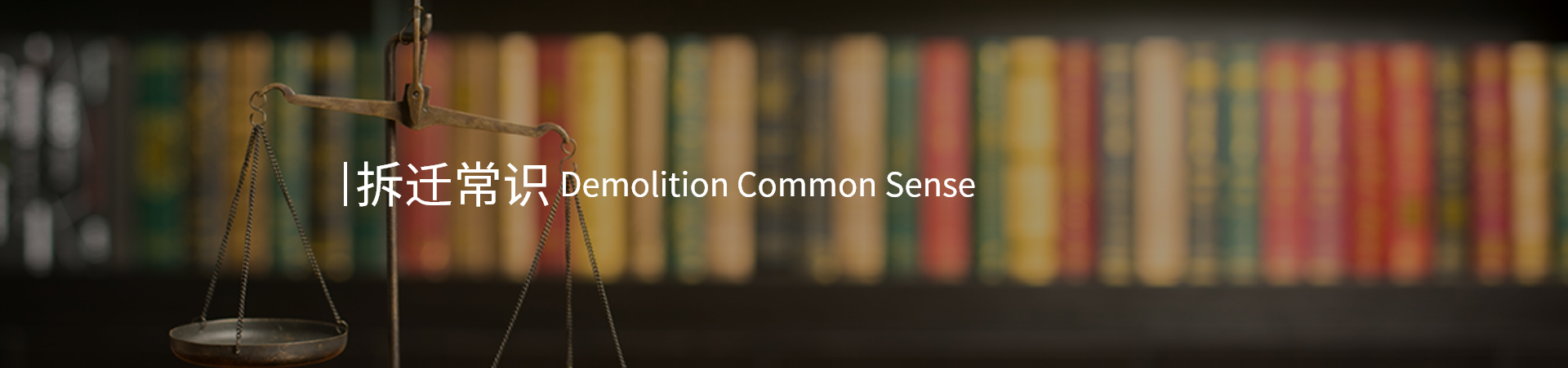“政府法定职责会‘过期作废吗?”——一纸“超期”答复背后的法律困境
导读:“难道就因为期限过了,政府就可以不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了吗?”王先生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解与愤懑。面对内蒙古呼伦贝尔海拉尔区政府以“超出安置方案征收期限”为由拒绝补偿的答复,他的疑问直指一个核心法律命题: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,是否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自然“过期作废”?
拆迁律师斩钉截铁地回应:“当然不可能!”这简短有力的回答,揭开了王先生六年艰难维权历程的序幕,也叩问着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。
1、六年悬案:被“期限”阻隔的补偿之路
2016年8月25日,一纸《房屋征收决定》改变了王先生的生活。他在海拉尔区合法拥有的房屋及院落被纳入征收范围。房屋所有权证、国有土地使用证、营业执照——所有证明其合法权利与经营活动的文件一应俱全。征收决定公告后,王先生却陷入漫长的等待。
六年时光流逝,直至2022年,他始终未收到海拉尔区政府作出的安置补偿决定。面对权利悬空,王先生多次向区政府邮寄《补偿安置申请书》,试图唤醒沉睡的行政职责。2022年8月22日,区政府的答复如同一盆冷水:“已超过安置补偿方案中的征收时间,故不予补偿。”
法律依据的缺失与“超期”借口的苍白,让王先生毅然走向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。而区政府在法庭上的辩词,更将“期限论”推向极致:“征收工作已完成,且原告申请超过《安置补偿方案》规定时间,应予驳回。”
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逻辑,以“超出安置补偿方案的征收时间”为由,判决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。
程序时限真的能够吞噬实体权利吗?这场败诉,将行政职责的持续性命题推至风口浪尖。
2、职责透视:安置补偿——无法回避的法定重担
要厘清政府职责是否“过期”,首先需审视其法定源头:
权责法定: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,市、县级政府对本区域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负有直接责任。征收决定的作出者,天然是补偿义务的承担者。
职责触发:该条例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,若签约期内未达成协议(如本案),房屋征收部门必须报请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并公告。
这绝非自由裁量权,而是法律设定的强制性义务。
在海拉尔区政府的答辩中,一个关键矛盾暴露无遗——其声称征收“已完成”,却又以“超期”拒绝对未补偿户履行义务。
征收进度的“完成”与法定补偿职责的“履行完毕”存在本质区别。 只要王先生未获合法补偿,政府的核心职责在法律上就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。
3、“持续状态”:击碎“过期论”的法律利剑
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:区政府超过《安置补偿方案》自设期限未履职,是否意味着王先生就此丧失诉权?
行政不作为的持续性特征:区政府自2016年征收决定后始终未对王先生作出补偿决定,此状态如未愈合的伤口,持续侵害其权益。
起诉期限的法定起算点:最高人民法院《行诉解释》第六十六条规定,对行政机关不履职提起诉讼,应自其“履行法定职责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”提出。
关键在于:若行政机关从未明确履职期限,或未告知诉权,如何确定“届满之日”?
拆迁律师指出,当行政不作为呈现持续状态时,侵害事实在行为终止前始终存续。王先生2022年的申请正是对持续侵权状态的抗争,而非新履职期限的起点。因此,其起诉完全在法定时效之内。
4、司法警示:再审曙光与“超期”裁判的误区
王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。司法实践中,类似案件常在一二审因“超期”理由败诉,却在最高法院再审中迎来逆转:“未履行补偿职责状态一直持续,原告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。”—— 最高法院在多起同类再审案件中的核心观点
海拉尔区法院的判决存在双重误区:
事实认定偏差:将《安置补偿方案》中的工作期限等同于法定职责履行期限,混淆了行政效率要求与法律义务边界。
法律适用错误:忽视行政不作为的持续性法律特征,错误适用起诉期限规定,变相豁免了政府的法定职责。
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睡眠者,但更不容忍职责上的沉睡者。当公民因信赖政府而等待,反被“超期”理由拒之门外,这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伤害,更是对行政诚信的侵蚀。
5、依法行政:职责永不“过期”的法治基石
海拉尔区政府以“期限已过”推脱补偿责任,暴露的是对权力本源的认知偏差。《安置补偿方案》中的时间节点是行政管理的抓手,而非切断法律义务的铡刀。法定职责源于法律授权,其存续由法律决定,不因内部计划时限而消弭。
王先生案揭示的深层警示在于: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背后,对每一户权利的尊重与保障才是法治文明的真正刻度。当政府以“超期”为由将公民拒之门外,其抵销的不仅是补偿款,更是公众对行政系统的信赖根基。
目前,王先生仍可依法上诉。此案终将走向何方尚未可知,但其提出的命题已振聋发聩:
在法治政府的框架下,没有任何一项目标可以压倒对个体权利的保障,没有一个“期限”能成为法定职责失效的免责牌。因为当职责被时间“赦免”,法治便失去了锚点。